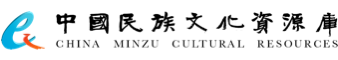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刚来中国的天主教内部就曾经发生过一次争执,利玛窦与他的同伴罗明坚在穿着上产生了分歧。耶稣会会士在刚进入中国时都穿着佛教的僧服,在中国生活10年之后,利玛窦建议改穿儒服,而罗明坚则坚持穿僧服,最后利玛窦获得了耶稣会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的支持,成为这场争执的胜利者。随后,耶稣会以利玛窦的亲儒为主要路线,执行文化适应策略,他们在生活方式上接受中国本土习惯,尤其是儒家士大夫的生活特点,以儒家的道德概念解释天主教的伦理,又以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天”和“上帝”来指称天主教的“God”。更关键的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敬天、祭祖、祀孔等行为进行了符合天主教的人文解释,从而使天主教有可能融入中国社会。然而,这种适应和融合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丧失了天主教的“纯洁”和“优越”。
在利玛窦死后,他的继任者龙华民率先反对以“天”和“上帝”翻译“God”,从而引发了耶稣会的内部争执。在1627年的嘉定会议上,耶稣会决定大致维持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只是禁用“上帝”一词,改用“天主”。然而,随着其他修会陆续到达中国,耶稣会内部的争论很快变成了修会之间的激烈冲突,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开始发酵。
1651年,中国的耶稣会派卫匡国赴罗马为中国礼仪辩护,他们以世俗化的语言重新表述的中国礼仪,被教廷接受并允许施行。随后,中国天主教经历“历狱”,所有外籍传教士都被赶到广州共同居住,他们借此机会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继续维持利玛窦规矩。
但是之后一些新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争论又开始激化。1681年,阎当到达中国。1693年,这位后来被康熙形容为“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的主教,在他的福建教区发布训令,要求禁行中国礼仪,于是争论再起。
为了为中国礼仪辩护,耶稣会在中国收集证据和辩词。这些证据资料出自许多中国信教人士之手,严谟就是其中之一。
严谟字定猷,福建漳州龙溪人,出生年月不详,大概在17世纪中叶。《龙溪县志》中记载他是贡生出身,他的妹夫曾经赴京参加会试,他的堂弟也曾参加科举考试,可见他的家族是个士绅家族。严谟的父亲严赞化是福建天主教开教人物艾儒略的学生,他自己也是自幼受洗,他的侄子也是天主教徒,这说明他的家族是典型天主教与儒家结合的家族。作为士人,严谟要去孔庙参加祀孔典礼;作为中国人,他要去祠堂参与祭祖仪式;作为天主教徒,他又要定期到教堂参加弥撒,这些都是他的人生赋予他的角色,他不得不起而辩护。对于像严谟这样的中国天主教徒而言,礼仪之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观念的冲突,更是切身的生活冲击与人生困境。
严谟一共写了10篇文章讨论中国的礼仪,涉及争论的几个关键问题。在《天帝考》一文中,严谟从中国古代经典中摘录相关论述,以讨论神的译名可否用“天”和“上帝”,这是对耶稣会内部争论的回应。反对者认为“天”是指自然之天或义理之天,与天主教的人格神完全不同;而“上帝”又出自中国古籍,具有很强的本土宗教内涵,不适合用来称呼天主教的神。而严谟反驳说,以“天”指称神就如以“陛下”指称君主,并不是以殿宇台阶为君主,而是不敢直呼其号,所以用他物代称。他表示“天主”不如“上帝”,因为在中国有天主、地主、山主的区分,因此天主会让人误以为只是天上之主,不如“上帝”意味着主宰一切。严谟进一步表示,如果强行用“天主”而不是“天”或“上帝”来指称“God”,就否定了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
严谟还仿照利玛窦《天主实义》一问一答的形式,写作了《李师条问》以回应教廷对中国礼仪的疑问。这些问答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主要并不是就中国礼仪进行学术讨论,而是为了反驳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祭祀礼仪的一些看法,因此很多是以他们的视角来提问。严谟尽力强调礼仪的人文性质,把祭祖视为后人对先人的纪念行为,表达祭者事死如生的追思之情;强调祭孔子是为了尊师重道,促进教化之意。这也是耶稣会来华之后的一贯策略,他们与儒家士人接触很多,熟悉这种伦理化的人文理解。
严谟在《辩祭》中说:“其礼不同,其时、其物、其人、其地又各不相同,则可知中国之祭,非与内外合一。”就是说,天主教追求内外合一,中国文化更在意差异与统一的结合,这体现了中西文化中一些更为根本的区别。中国礼仪的差异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同样的礼仪,有人视之为神,有人视之为文,有人祈求福报,有人怀思先人,有人追功报德,有人消灾解难,这是中国礼仪与天主教仪式的差别。《论语》中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代表着中国人对祭祀问题的关注角度,是在祭祀的人而不是所祭祀的对象。严谟进而引用了《礼记·祭统》中的一句话:“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说明中国礼仪并不注重外在的祭祀对象,而强调一种主体体验。一个共同的仪式和主体的不同体验,意味着外在的“一”和内在的“多”的结合,构成了一个成功包含“一”与“多”的秩序。只要认同这个秩序的基本核心——儒家的伦常,有着不同信仰的人就都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国文化也就成功地将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以及天主教纳入这个秩序之中。这也正是中国文化强大包容性的体现。
严谟为中国礼仪的辩护指出了中国文化包容性的根源,但是罗马教廷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文化的这一伟大精神。当中国人以其特有的包容性接纳天主教时,天主教却以内外合一的“纯洁性”排斥中国人的传统与生活。
1704年11月,教廷颁布《至善的天主》教谕,正式禁止中国礼仪。1721年,在经过多次劝化无果之后,康熙皇帝下谕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中国天主教成则因利玛窦的中国化策略,败则因去中国化的礼仪,由此进入了灰暗的历史之中。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