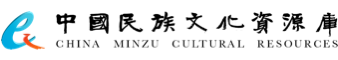
近日,由中国人口学会民族人口专业委员会主办的2018年中国民族人口学术研讨会在银川市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大学等科研院所的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新疆人口的发展变动,少数民族人口的结构、教育、婚育以及迁徙、脱贫与幸福感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指出,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是我国人口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人口问题与国家生育政策及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密切相关。研究好少数民族人口问题,提出恰当的政策建议,能为实现我国人口均衡化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本文特集纳了此次学术研讨会上部分学者交流的研究成果,希望对读者了解我国少数民族人口问题有所启发。
1 结美满姻缘,从族际通婚看各民族交融发展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是让各族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成美满姻缘。各民族之间的通婚,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沈思通过对族际通婚的定量分析,勾勒出近年来我国族际通婚的基本状况及各民族交融发展的态势。
12个民族的族际婚超过族内婚
关于族际通婚的研究,过去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因为能利用的数据少。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首次公布了不同民族通婚的具体数据,随后定量研究成果逐渐增多。
“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有配偶的夫妇中,属于族际通婚的有1706.74万人,占已婚人口的3.01%,比2000年增加了81.24万人。
数据显示,56个民族的族际通婚率差别较大,2000年至2010年,绝大多数民族的族际通婚率基本稳定,体现出各民族交融发展的态势。其中,有12个民族的族际通婚率超过50%,即族外婚比例超过族内婚比例。这12个民族分别是鄂伦春族(88.63%)、赫哲族(87.44%)、俄罗斯族(85.54%)、高山族(80.36%)、锡伯族(75.53%)、塔塔尔族(71.37%)、鄂温克族(70.93%)、京族(63.71%)、达斡尔族(58.98%)、畲族(54.94%)、仫佬族(52.38%)和乌孜别克族(51.76%)。
这12个民族中,除畲族外,均是人口较少民族(人口总数在30万以下),其中人口在10万以下的民族有8个。
56个民族中,有6个民族的族际通婚率低于10%,分别是藏族(7.16%)、柯尔克孜族(4.29%)、哈萨克族(4.2%)、塔吉克族(2.84%)、汉族(1.45%)和维吾尔族(0.53%)。
这6个民族中,有4个民族人口基数较大:汉族和维吾尔族人口在千万以上,藏族和哈萨克族人口在百万以上。而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则居住在帕米尔高原,地理位置偏远,人口流动性差。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一般来说,各民族的人口规模直接影响族际通婚的绝对数量,人口少的民族族际通婚率高,人口多的民族族际通婚率低。而居住地理条件、人口流动性等因素,也成为制约族际通婚的重要因素。
少数民族形成了九大通婚圈
由于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民族的地域分布对族际通婚也有着重要影响。根据各民族的主要通婚对象和通婚率,可以将除汉族外的55个少数民族归为九大通婚圈:
一是回族通婚圈。居住在青海、甘肃、新疆等地的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受人口规模及宗教信仰影响,以回族为主要通婚民族。
二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通婚圈。居住在新疆的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同样因为人口规模及宗教信仰原因,以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为主要通婚民族。
三是壮族通婚圈。居住在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的瑶族、仫佬族、毛南族和京族,以当地人口较多的壮族为主要通婚民族。
四是藏族通婚圈。居住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的土族、羌族、裕固族、门巴族和珞巴族,以当地人口较多的藏族为主要通婚民族。
五是苗族通婚圈。居住在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广西、重庆等地的布依族、侗族、土家族、水族、仫佬族和仡佬族,以当地人口较多的苗族为主要通婚民族。
六是彝族通婚圈。居住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白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布朗族和基诺族,以当地人口较多的彝族为主要通婚民族。
七是白族通婚圈。居住在云南等地的傈僳族、纳西族、阿昌族、普米族和怒族,以当地人口较多的白族为主要通婚民族。
八是傣族通婚圈。居住在云南等地的景颇族、阿昌族和德昂族,以当地人口较多的傣族为主要通婚民族。
九是东北通婚圈。居住在内蒙古、黑龙江、辽宁等地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赫哲族和锡伯族,以蒙古族、满族和达斡尔族为主要通婚民族。
由此可以看出,民族人口的地理分布,决定着族际通婚的广度和深度。
46个少数民族通婚率最高的对象是汉族
“六普”数据显示,虽然每个民族都与其他民族有着通婚关系,而且主要通婚对象差异较大,但所有的少数民族都与汉族有通婚关系。其中,有46个少数民族通婚率最高的对象是汉族。高山族、俄罗斯族、鄂伦春族和赫哲族这4个民族以汉族为其主要通婚民族,通婚率在65%以上。
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民族的女性族际通婚率要高于男性。2010年,42个民族的女性族际通婚率高于男性,其中9个民族的女性族际通婚比例高出男性的1倍以上,且女性的流动率均高于男性。这9个民族分别是哈尼族、黎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景颇族、德昂族、独龙族和门巴族。
仅有两个民族的男性族际通婚率远高于女性,分别是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这两个民族属于人口较少民族,居住在新疆边境地带,主要通婚民族是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
随着近年来各民族人口跨区域流动空前增加,族际通婚愈加频繁。根据对2015年总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21岁至35岁年龄段的族际通婚人数占比高。调查还显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增加了族际通婚的可能性。
2 各民族幸福感普遍提升
“你幸福吗?”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幸福感越来越受到关注。调查显示,新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幸福感明显提升。如果细究,各民族的幸福感又如何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周祝平对几个人口较多民族的幸福感进行研究,发现了一些特点。
调查显示,在汉、满、蒙古、回、壮这几个民族中,回族的幸福感最高,2015年感觉“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总人口比例达91.7%;而蒙古族感觉“非常幸福”的人口比例最高,达36.7%。
调查还显示,2003至2010年是各民族幸福感提升最快的时期,汉、蒙古、满、回、壮这5个民族感觉幸福的人口比例分别上升了35.1、27.6、35.2、45.0和35.5个百分点。但是,2010年至2015年各民族的幸福感提升速度都明显放慢,平均不足10个百分点,壮族甚至还下降了5个百分点(如左图)。
各民族幸福感提升速度放缓,甚至遭遇瓶颈,符合“伊斯特林悖论”(或称“幸福悖论”)。该理论认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财富的增加并不能带来幸福感的相应增加。各民族在经过了物质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幸福感提升后,未来幸福感的继续提升将更多依赖非物质因素,即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3 迁移流动,深刻改变边境人口结构
我国陆地边境线近86%位于民族地区,有30多个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这决定了我国边境人口具有显著的地域及民族特征。随着边境交通基础的改善及“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等建设,人口流迁逐渐成为边境人口自然结构改变的重要因素。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蔡果兰通过对内蒙古、广西、云南、黑龙江、吉林、新疆等边疆六省区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及实地调研,对近年来边境人口的流迁走向及特点有了初步研判。
务工经商是人口流入边境地区的主因,青壮年是主力
2010年,边疆六省区人口流入原因多样,最主要的是务工经商,云南最高达52%,吉林为27%。到了2015年,这种倾向更为明显,云南、吉林流入人口中,务工经商者均达80%以上,其中还伴随着家属随迁。
从流入人口的地域可以看出:一是黑龙江和新疆对比明显,黑龙江70%以上是省内跨市流入,而新疆70%以上是跨省流入;其二,广西与内蒙古人口流入结构相同,40%以上跨省,30%以上跨市,20%跨县;其三,云南与吉林类似,都是省内跨市流动略高于跨省流动。
2015年,边境流入人口有一大共同点,就是均为青壮年,其中内蒙古流入人口年轻态最显著,最大的储备年龄是25岁至29岁;其次是新疆、广西、云南,吉林与黑龙江相比较而言呈壮年化,40岁至55岁年龄段偏多。
边境地区净流入和净流出现象并存
由于对外开放带来的边贸红火,很多边境地区出现了人口净流入现象。如广西凭祥,流入人口大都做生意,主要经营红木、水果、越南特产等。由于中越两国边民来往方便,很多越南人乐意到中国打拼,包括不少年轻妇女。大部分本地人觉得,外来人口的流入带动了凭祥的发展。
内蒙古二连浩特是类似的状况。二连浩特作为与蒙古国接壤的口岸城市,与蒙古国的商品贸易来往密切,加之当地人十分友好,生活环境安逸,吸引了不少青壮年群体前往经商。当蒙古国经济形势好时,二连浩特流入人口能达到本地人口的两三倍。
但在吉林延边的边境乡镇,却出现了人口净流出现象。当地朝鲜族青壮年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加上与韩国的历史渊源,很多群众尤其是大量妇女外出务工经商,主要流出地在韩国和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北京、上海、山东、广东等省市。当地甚至出现了一些“空心村”“光棍村”,人口数量锐减,人口结构失衡。
4 新疆人口的变动趋势及面临的挑战
新疆作为边疆多民族聚居区,在决胜全面小康阶段,发展和稳定的问题十分突出。人口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新疆人口问题得到学界普遍关注。
本次研讨会特开辟了“新疆人口”单元,南开大学教授原新、新疆大学教授艾尼瓦尔·尼吉木和副教授热衣拉·买买提、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马胜春、河北大学副教授王朋岗等围绕新疆人口变动与生育政策、人口与经济均衡发展、人口与就业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新疆人口的变动趋势
占我国国土面积约六分之一的新疆,有13个世居民族。2016年,新疆总人口达2398.08万,其中维吾尔族1144.9万人,占47.74%,汉族826.95万人,占34.48%,两者合占全疆人口的82.22%。
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外来人口不断增加,维吾尔族人口在全疆的比重由1949年的75.95%下降到2016年的47.74%。但是,维吾尔族人口的绝对数量却呈现较快增长势头。
据统计,1949年维吾尔族人口为329.12万,到2016年已增加了2.48倍,保持年均3.7%的增速,年均净增12.18万人。维吾尔族人口数量的增长,与我国对农村和少数民族实施较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
如果将新疆分为北疆、东疆和南疆三大地理板块,伴随着这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维吾尔族人口的分布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维吾尔族人口绝大部分聚居在南疆,其后维吾尔族逐渐向北移,而汉族则有南移的趋势。因此,南疆维吾尔族人口比重由1953年的88.08%下降到2016年的82.95%,北疆维吾尔族人口比重则由1953年的7.13%上升到2016年的11.89%,东疆维吾尔族人口则由1953年的4.79%上升至2016年的5.16%。
新疆人口增长面临的挑战
根据学者们的分析,目前新疆人口呈现如下发展走向:
一是新疆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其中汉族人口已经属于典型的老年型,且其少子老龄化的程度比全国平均水平更加严重;而少数民族人口属于成年型早期,比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平均水平更加年轻。
二是目前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类型处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阶段,这也决定了其少儿抚养比高达35.99%,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加,就业压力增大。
三是新疆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发展呈现不均衡性,人口较快增长抵消了经济发展的部分成果。同时,由于人口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能形成的现实人力资本大打折扣,不利于经济快速发展。
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尤其是南疆农村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人均耕地和牧草地资源减少,使当地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面临更严峻的压力;另一方面,人口抚养比高,导致很多家庭经济负担过重,不但加深了贫困,还直接影响到孩子受教育水平,有可能造成下一代继续贫困。同时,大量适龄劳动人口不能及时就业,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安定因素。
作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南疆四地州的脱贫攻坚问题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为解决当地劳动力外出务工难等问题,在对口援疆政策的帮扶下,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落户南疆,吸纳维吾尔族青年进厂工作,产品由对口支援的省份帮助销售,不但就近解决了不少维吾尔族青年的就业问题,而且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