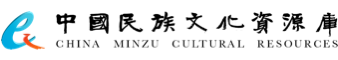
光影中的异乡似乎总带着一种变幻的神秘气质。不管是静谧的风景,或是曼妙的歌舞,乃至陌生的语言、独特的建筑,都在银幕中透露出迷人的质感。当我们动容于异域文化新鲜的视听冲击力时,便会不自觉地反思自我,反思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兴奋带来的眩晕感和灵光一现的顿悟都在此时发生了。
文化是具有共性的。我们也许难以感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主人公对传统生产方式的依赖,对故土“不可救药”的眷恋,对“外来者”无限宽容的善良,但在内心深处,却接受并认同这种带有强烈中华民族烙印的文化心理。这里的人们纯朴、勇敢,牢牢守护内心的道德感而显得拙于变通;这里的历史热血、直接,野性的力量中饱含温柔的坚持;这里的爱情发乎情止乎礼,却有生死相守的痴情;这里的离别克制、留白,却如潭水千尺,魂牵梦绕。
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充分保留本民族特色的同时,必然传达着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这种传承,正是《伊犁河》中回、汉两族家庭对亲情的固守与牺牲,是《德吉德》中草原母亲坚强而博大的人性光辉,是《五彩神箭》中蕴藏于古老壁画与羌姆舞中的精神皈依,是《侗族大歌》中穿越岁月潮汐的天籁之音。

乡愁:根植于民族的文化基因
我们从咿呀学语时就会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古诗中那份切切的乡情如同隐藏在民族文化中的基因,让我们深深依恋故土。
《伊犁河》中,这份乡愁隐藏于山谷间、河畔旁的蜂场。在这里,一户回族人家经历了多次骨肉分离,却始终念念不忘那个象征着团圆的地方。曾经渴望大城市的儿子阿尔萨在上海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后,却发现自己依然深深思念家乡的回族母亲,并通过高考终于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父亲尤素甫经历了异乡漂泊流浪后,在记忆恢复的第一时间,也急切地赶回伊犁河畔寻找妻儿。而女主人公法图麦,则始终孤独而执拗地守候在那座盛满了回忆的木屋旁。逝者如斯,然而思念不止。一条时而舒缓时而凶险的河,一座隐藏在青山绿水间的木屋,一户相亲相爱却不能团聚的家庭并非仅仅是伊犁有着如此令人欲罢不能的向心力,而是离别后的故乡,不管变换出千万种模样,总能令人心心念念的渴望。
乡愁并非离乡者独有。如果说《伊犁河》展现了一种纯朴而直接的乡愁,那么《德吉德》在乡愁中则更添几分焦虑。在被厚厚的白雪包围的蒙古包里,草原母亲德吉德甘之如饴地重复着牧羊女的生活。她放弃了留在城里拥有一份体面工作的机会,嫁给了草原上最有名的驯马师,传承了母亲支撑起家庭的责任感,因为她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快乐。一场雪灾带给她前所未有的艰难,也让她更加确信自己对草原和家人的热爱。她对游牧文明的天然依恋和那份淡定从容,在蒙古包中散发着神性的光芒。惜字如金的台词里,反复出现了“快乐”。这正是蒙古人的生活信念和目标。没有了快乐,家财万贯、穿金戴银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影片的最后,为了给丈夫治病,一家人启程迈向城市时,德吉德这样坚定地说:“治好伽森麦的病就回来,有一只羊就会变成一群羊。”
《五彩神箭》中则通过对古老精神的传承,寄予了藏族同胞对祖祖辈辈悠久历史宝藏的挚爱。尖扎县的射箭比赛引发了男主人公桀骜不驯的一面,而他的对手正因恪守传统而屡屡获胜。影片在冲突中鲜明地表现了对藏族文化的敬畏,作为羌姆舞领舞者的扎东,无疑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化身。通过人物内心的成长,我们看到了曾照亮无数先人的文明之光冉冉升起,生生不息地闪耀在藏民心中。这种回归,正是对古老乡愁的重拾。火种不灭,文化不灭,则故乡永恒。
无独有偶,《侗族大歌》中的歌师们也在用自己的一生,去唱响乡音的清澈与嘹亮。爱情和友情可以被理性所掩盖,容颜和山谷可以被时光所改变,但如诗般的回忆和歌声却永远环绕在脚下这片挚爱的土地上。

苦情:缺憾美的想象空间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缺憾”一直有种独特的审美偏好,从癫狂的草书到瓷器上的裂纹,从殉情的梁祝到含恨而逝的林黛玉,都无一不让人心神摇曳,如痴如醉。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说:“悲剧能使人在精神上变得高尚,使他们从日常生活的琐碎贪求中解放出来。”也许,缺憾美也如此。
命运的齿轮在法图麦身上错位地运转着。在夫离子散后,她仍割舍不下伊犁河畔的木屋,尽管那里夜晚漆黑寂静,让恐惧和思念更加疯狂地生长。尽管只要自私一点,就能把儿子留在身边,但内心善良的她,把所有的苦难独自吞下。在近似执拗的自我牺牲中,她把最好的未来献给了亲人,而将无垠的等待留给自己。故事的结尾,如同宿命般沉痛,法图麦错过了与丈夫、儿子的重逢。“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是,这回响来得太晚,只有遗憾和惋惜。
在《德吉德》纪实镜头和平淡叙述的背后,我们依然能捕捉到那种藏在人物内心无法被填满的缺憾。丈夫伽森麦去城里开饭馆,却因为恪守着草原人热情好客的传统,不愿让金钱破坏这种友谊而导致生意惨淡,内心挫败。另一方面,作为妻子的德吉德尽管默默支持丈夫,从未怨声载道,却也不免对失去顶梁柱男子气概的丈夫感到些许失望。在失望之余,则是更深的理解与疼惜。隐忍而心照不宣的家庭矛盾,最终以伽森麦的病情加重而举家迁徙划上了句号。“没有人比我更懂他!”德吉德对着镜头平静地说。然而冰冷的现实如无情的积雪,随着牛车的铜铃声,伴随在他们前行的路上。
《侗族大歌》的故事中,三位主人公都经受着爱情与友情的煎熬。他们将爱视为生命,却因责任和理性的驱使,忍痛割爱,不能终成眷属。即便在最终皆大欢喜的《五彩神箭》里,相爱的一对情人也曾遭遇了重重阻挠,险些因家族恩怨而放弃爱情。

城市与故乡:砒霜与蜜糖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正是现代城市文明与故乡草根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可可西里》中以令人震撼与反思的效应,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生存状态的残酷,以及自然生态中精神信仰的危机。我们正讨论的这四部电影,虽然并没有像《可可西里》一样振聋发聩地将冲突作为主题,但仍然以令人无法忽视的笔墨,刻画了二者碰撞中若隐若现的棱角。
在《德吉德》中,导演卓·格赫用大量篇幅描述女主人公德吉德在乌珠穆沁草原中艰苦却恬淡的日常生活。她生煤炉、热奶茶、熬骨汤、凿冰取水、为动物接生,精心哺育自己的两个孩子,在深雪中长途跋涉寻找迷失的羊羔,与母狼航辛保持着警惕与帮助的双向互动,甚至让失去母亲的小羊羔和自己的孩子共同享受母乳的滋润。德吉德与自然和生灵之间的关系,无不展现了草原文明最原始而美好的状态。然而这种美好,从影片初始,就潜藏着一种不安。现实的无奈在丈夫伽森麦身上,露出了令人深刻痛苦的本质。城市与故乡——彼之蜜糖,吾之砒霜。伽森麦说:“大家都是朋友,我们蒙古族男人不能收朋友的酒钱,自由地喝酒唱歌多好。”曾经作为草原上最好的驯马师,如今却面对着生意的破败和家庭的压力,伽森麦在经历了城市文化的强势入侵后,依然坚守着草原文明最后的绿洲。德吉德的母亲是上一代牧场文化中杰出的女性代表,“功成身退”地安享晚年;弟弟在城里做公务人员,前途一片光明;懂事的大女儿俨然即将成为下一代的草原守护者。这个家庭中不同身份的人,分别展现了城市文明触角深入草原文明的过程中,各自的价值选择与出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最终不得不向城市迁徙,或许也意味着草原文明必将面对新的蜕变。
相比于《德吉德》中对蒙古人性情的原生态展现,《伊犁河》似乎在民族特征上不那么突出。依赖故乡的母亲、向往城市的儿子、生活的变迁与成长的感悟,在世俗每个角落里的家庭中都上演着、发酵着。这种普世的、共性的情感,无关民族,无关地域。导演用伊犁的村庄和上海这个现代化都市之间的落差,诠释着亲情与文化。影片的结局无疑做出了选择,无论城市的人群多么川流不息,也比不上童年在故乡与亲人的耳鬓厮磨。
《五彩神箭》里的扎东,由反叛青年到成熟男人的过程,正是从藏族的古老文化中找到了蜕变的催化剂。对胜利的渴望让他失去自信,舞步凌乱,甚至用现代弓箭违规比赛。这在扎东的父辈们看来,无疑是对古老传统的背叛。在父辈的传承下,“拉隆贝多射杀朗达玛”的故事在神秘的壁画中、雄武的羌姆舞中,神秘而威严地蕴藏着。这种对寻根诉求的一再强调,或多或少反映了民族文化在面对现代文化入侵下的焦虑。结尾的比赛中,县文化局规定使用现代弓箭,而扎冬在盆栽里抓了一把土,似乎也暗示着传统与现代能够和谐共生的倾向。
《侗族大歌》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对侗族文化的探寻与纪念之旅。导演丑丑2003年在贵州省黎平县岩洞村遇到了一位90多岁的老歌师,正是老歌师的生平故事,触发了导演深藏于心的侗歌情节,将之写成剧本。作为从侗寨苗乡走出来、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年轻导演,丑丑用十多年的寻根信念,在银幕中点亮了贵州青翠绵延的山谷、侗寨月明星稀的朗夜和那悠扬美妙的侗族大歌。而千里之外的城市中,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喧哗与躁动。在这个从生存方式到价值观念都在微妙变化的时代,对故乡与传统的忧思,总会令我们心生惆怅。

类型化与艺术性的双重探索
在以商业票房和娱乐性为第一追求的电影生态中,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往往被归类为小众片、文艺片,在院线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提起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普通大众的记忆似乎总是最先筛选出《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这样脍炙人口的经典,或《可可西里》、《图雅的婚事》等由第六代导演完成的作品。真正以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工作者视角展现的原生态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如夜空中的繁星,遥相呼应,星星点点,似乎还在等待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然而可喜的是,在院线片猛烈夹击的当下,我们依然能有幸看到这样的佳作。
导演万玛才旦2002年就以短片《静静的嘛呢石》获得多个奖项和好评,新作《五彩神箭》则刚刚获得第1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的提名、金爵奖最佳摄影奖。在电影叙事方面,本片与好莱坞经典叙事结构不谋而合,人物性格与冲突的设置、情节的发展和走向,都是非常规整的剧情片模式。比如主人公由叛逆到成熟,由骄傲的不驯者到敬重神灵与传统的技艺传承者,印证着古今中外关于“成熟”这一过程的诠释。将不同阶段的几次比赛,用不同的形式,展现出剑拔弩张的紧张感,在节奏上层层递进,最终得以升华,也非常符合观众的观影习惯。《五彩神箭》在向主流的靠拢中,似乎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条可供学习的道路。既具有世界性,又不失民族性,何乐而不为呢?
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形式上,《德吉德》开创了另一种具有艺术想象力的模式。《德吉德》是一部纪录片式的电影,没有花哨的调度与叙事化的蒙太奇,镜头始终显得冷静而客观。如果不是几次类似“穿帮镜头”的持镜者画外音,我们几乎意识不到有“外人”的存在。镜头并不指引或间接暗示某些讯息,而是完全跟着人物的一举一动,追随着蒙古包内外的世界。饰演主人公德吉德的女演员并非职业演员,她只是草原上一个普通的牧民,也正因如此,片中对劳动细节的表现,也分外自然而真实,一举一动都娴熟似家常,那是受过训练的专业演员也无法准确传达的从容。在叙事层面,《德吉德》也摒弃了一切生硬的规则和套路,如一幅徐徐展开的草原画卷,没有尖峰时刻的刺激,却有细水长流的精彩,散发着引人入胜的魔力。
《伊犁河》在时间和地域上跨度之大、景色风情之优美壮阔、音乐之情感磅礴,都有史诗电影的潜质。但与传统的英雄史诗电影不同,《伊犁河》讲述了因时代变迁而联系在一起的两对家庭的心灵史诗。整部影片是一个大的闪回,抒情的细节勾起了我们对故事发展的好奇。当影片落幕,我们为主人公的悲欢离合扼腕叹息,也见证了爱的伟大与极致。也正是这种特质,让本片区别于普通的剧情电影,产生了超越民族的国际视野和深切的人文关怀。
与北方的深沉大气相比,拍摄于贵州的《侗族大歌》则处处透露着南方的钟灵毓秀。安详的古镇,玲珑的山水,悦耳的歌声,整部影片的基调是婉约的,故事情节也充满着中国独有的千回百转、柔肠寸断。《刘三姐》之后的以民歌元素为主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还没有哪一部真正调动起了全民热情,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历时4年打造的《侗族大歌》在各方面都显露出再续经典的雄心,也表现了精心制作的诚意。也许,它会成为民族题材电影中一个崭新的类型,一次丰富的创造。

电影《伊犁河》剧照
链接:
第六届北京民族电影展故事片展映
本届民族电影展共展映故事片11部,其中《公主为奴》(蒙古族)、《五彩神箭》(藏族)、《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裕固族)、《迁徙》(羌族)这4部影片各放映5场,由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向社会售票。
本届民族电影展选取《启功》作为开幕影片。据北京民族电影展主席牛颂介绍,这一方面是因为启功作为满族爱新觉罗家族的代表人物,为民族团结和文化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另一方面是导演丁荫楠等人拍摄这部大师传记影片所体现出的文化使命感,具有示范意义。
4部民族电影向社会公开售票放映,标志着民族题材电影质量的提升。其中,表现青海尖扎地区藏族传统射箭文化的《五彩神箭》,曾入围上海电影节金爵奖;《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聚焦生态变迁和裕固族文化传承,入围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这些影片之前已在业界获得了好评。
除了展映部分,设在中华世纪坛的北京民族电影展展位,还邀请了多位嘉宾进行访谈,包括《公主为奴》、《海鸥老人》、《剑河》等影片的主创,民族志纪录片的导演、研究者等。此外,《古格王朝》、《楼兰》、《狼女》、《十万大山》等电影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