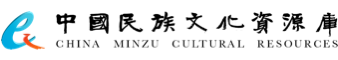
综观中国民族古文字在漫长历史中的使用和流行,有以下特点:
一、少数民族文字与汉文同时使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成为我国的主题民族,汉文的通行范围很广。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少数民族一般居住在我国边疆或山区,少数民族文字大都在其居住地使用。我国西北地区流行的文种最多,佉卢字、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察合台文流行于新疆地区;回鹘文在新疆、甘肃一带使用;西夏文适用于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在北方和东北地区有突厥文、契丹文、女真字、回鹘式蒙古文、老满文。藏、青、甘、川、及云南藏区有藏文。云、贵、川、桂地区则有彝文、水书;云南有东巴文、哥巴文、傣文、白文。广西有方块壮字。四川有尔苏沙巴文。即使在通行少数民族文字的地区,也往往是汉字和民族文字并用,有时甚至汉字的使用更为广泛。
有的少数民族尽管一度在全国成为统一政权中的主体民族,但其民族文字始终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例如八思巴字在创立以后,于至元元年(1269年)颁诏全国推行,译写境内一切有文字的语言,除记录蒙古语外,还用于书写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等,虽经元朝政府大力推行,但仍未能广泛应用。最后随着元朝的灭亡,这种文字也渐被废弃。满文在17世纪创制后,也未因满族成为全国的统治民族而普及全国,它虽经大力推行,并被尊为“国书”,也只是在一段时间和一定范围内使用。
二、中国民族古文字互相之间往往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在临近地区,关系更为密切。这些关系大体上可分为三种:
(一)互相影响
不少民族文字是参照其它文字创造或改制的。有的是系统地借用了其他文字的字母,如回鹘式蒙古文是在回鹘文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有的是对其它文字的形体和书写形式做了一定的改变,如在横写的藏文基础上制成了竖写的八思巴字。有的是参照了别种文字的笔画,如西夏文大多数字是用了类似汉字会意和形声的方法构成的。还有基本上利用了别的文字,或对一些字合并、增删笔画,如方块白文和方块壮字都属于这一类。
(二)同时使用
一个民族在一段时间里往往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字。粟特人在突厥化过程中同时使用粟特文和突厥文。回鹘文和阿拉伯字母的文字在新疆不同地区操突厥语的民族中间并行五百余年。纳西族以汉文作书面交际工具,而民族文字东巴文在东巴经师中流传。辽代汉字、契丹大、小字三种文字并行。金代前半期,汉字、契丹大、小字和女真大、小字五种文字并用。在西夏时期,西夏文和汉文同时使用,就连皇陵中的碑文也是用西夏文、汉文两种文字书写的;当时还使用藏文。元至正五年(1345年)在居庸关过街塔基门券洞内,用梵、藏、汉、回鹘、西夏、八思巴六种文字镌刻了陀罗尼经和造塔功德记。原立在黑龙江口的有名的《永宁寺碑》是用汉文、女真字和蒙古文三种字刻写的。这种刻有多种民族文字的典型文物,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多种民族文字同时使用的情况,是我国古代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例证。
(三)承前接后
有些民族在历史上使用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字。维吾尔族的祖先曾使用过突厥文、回鹘文,后来又使用察合台文和现在的维吾尔文。蒙古族先后使用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字和现在的蒙古文。女真族先后使用过契丹字、女真字和蒙古文。其后裔满族创制满文前使用过蒙古文,后来又先后使用无圈点老满文和有圈点满文。还有一些民族在创制自己的民族文字之前使用汉文,如党项族、壮族、白族等,女真族创字之前用汉文和契丹字。这种前后承接的使用,往往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新的文字产生后,原来所使用的文字仍继续通行一段时间。
三、用本民族文字翻译其他民族的文献是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
回鹘文佛经是先后从焉耆-龟兹文、汉文、藏文移译过来的。西夏文佛典也译自汉文、藏文,并用藏文为西夏文经注音。又如八思巴字蒙古文《萨迦格言》译自藏文。用各种民族文字翻译汉文著作更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如藏文《战国策》、《大唐西域记》译自汉文。用彝文译《太上感应篇》、《唐僧取经》、《唐王游地府》。如用傣文译汉文《西游记》、《儒林外史》。用契丹字译的汉文书籍有《论语》、《孟子》、《孝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贞观政要》、《类林》等。用女真字译过《孝经》、《贞观政要》。用回鹘式蒙古文译过《孝经》,用八思巴文字译过《百家姓》。为了学习对方语言、文字和翻译的需要,出现了一种文字给另外一种文字注音的字书。焉耆-龟兹文文献中有古龟兹语-回鹘语、梵语-龟兹语对译字书。八思巴字为汉字注音成《蒙古字韵》一书。《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文、汉文互注音、义的双解语汇本。明清两代的《华夷译语》中的《高昌译语》、《女真译语》、《西蕃译语》、《倮倮译语》等也是为当时的翻译工作而编的工具书。清代的《五体清文鉴》是在这一优良传统基础上的新发展。
编辑:王韵茹
参考资料: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